MCP已死、80%App将消亡、Vibe Coding是侮辱:OpenClaw创始人的一人团队如何创造全球现象级产品?
Lex Fridman Podcast的第491期,也采访了最近最火爆的AI嘉宾Peter Steinberger,OpenClaw创始人。由于谈的时间长(超过三小时),这基本是Peter近期所有访谈中信息密度最高的一期了,覆盖了agentic engineering(智能体工程)的工作流演进、AI编程的实操方法论、创始人心态,以及OpenAI和Meta同时抛出橄榄枝的幕后故事。所以我就再发一期OpenClaw的内容。最近OPC(一人企业)这个概念很火,这个哥们是地表最强OPC了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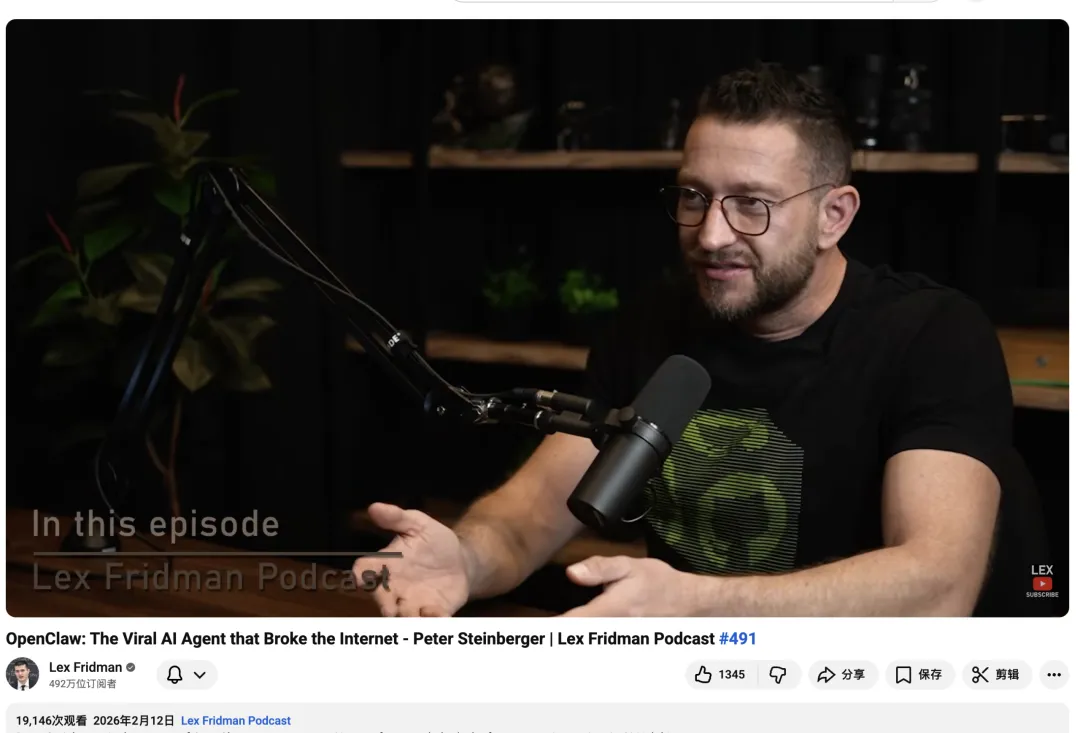
我之前就有预感扎克伯格一定会想来收购的,甚至我觉得小扎看到OpenClaw,播客中也证实了,我想小扎应该已经后悔花大价钱收购Manus。
为不了解Peter和OpenClaw的朋友介绍一下背景。Peter曾花13年打造PSPDFKit(一个装在10亿台设备上的PDF SDK),卖掉公司后消失三年,2025年11月用一个小时搭出OpenClaw原型,三个月后做出GitHub史上增长最快的开源项目——17.5万星标,一周200万访客,前Tesla AI总监Andrej Karpathy称它是”我近期见过的最接近科幻起飞的东西”。
OpenClaw是一个开源AI智能体,接入WhatsApp、Telegram、Discord等聊天工具,在用户本地设备上运行,拥有系统级权限,能替你操作电脑上的一切。
Peter说,编程作为一种手艺正在消亡,但构建(building)作为一种能力正在爆发。”虽然OpenClaw是一个自动化AI产品,但”那些试图把所有事情自动化的人,做出来的东西缺少风格、缺少爱、缺少人味。”
1. 一个小时原型:为什么大公司做不出来
Peter从2025年4月就想要一个AI私人助理。他试过把自己和朋友之间的WhatsApp聊天记录喂给GPT-4.1的百万token上下文窗口,然后问模型”这段友谊为什么有意义”。模型从海量日常对话中提炼出了很深的洞察,他把结果转给朋友看,朋友们读完都流泪了。但他当时觉得大厂肯定会做这个,就搁下了。
到了11月,没人做出来。他烦了,直接动手。
第一版原型的核心架构极简:把WhatsApp消息通过CLI(命令行工具)转发给Claude Code,拿到回复再发回WhatsApp。”一个小时就搭好了。”但他不满足于纯文本,花了几个小时加上图片支持,因为他认为截图是给智能体提供上下文最高效的方式。
为什么大公司做不出来?Peter在播客里没有直接回答,但他的行为本身就是答案。他不开会、不做PRD、不等法务审查。想到就做,做完就发。“今天写代码,明天就能上线。”他在访谈中反复强调,OpenClaw之所以赢,是因为”他们都太把自己当回事了”。大公司需要协调、审批、安全审查,一个功能从构想到上线可能要几周甚至几个月。而他一个人,直接上线。
这种速度在代码量上也能体现。2026年1月,他一个人提交了6600个commit。整个项目目前有30万行代码,支持几乎所有主流聊天平台。
2. Agent自学语音:通用编码能力的真正含义
在摩洛哥马拉喀什旅行时,Peter随手发了一条语音消息给自己的智能体。他压根没给它加语音功能。
结果智能体自己检查了文件头,发现是opus格式,用ffmpeg转码,又翻到了本地存储的OpenAI API Key,用curl把音频发给Whisper API做转写,然后回复了他。更聪明的是,它没有选择下载Whisper本地模型(太慢太大),而是判断出调用云端API才是最优解。
“我当时就想,这玩意儿怎么做到的?”
这个故事在播客里反复被提起,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关键洞察:大模型的”编码能力”其实不是编码能力,是通用问题解决能力。模型不是在”写代码”,它是在理解一个问题(收到了未知格式的文件),搜索可用工具(本地CLI和已有的API密钥),评估方案(本地模型太慢vs云端API更快),然后执行最优路径。这种能力可以迁移到任何领域。
Peter后来在Discord上公开了自己的智能体,安全措施几乎为零——只是在prompt里写了”只听我的”。黑客来了,他就在旁边看着,继续用智能体开发智能体本身。他的理由是:”人们必须亲身体验才能理解。”从2026年1月1日开始,项目真正起飞。
3. Soul.md:AI写给自己未来的信
Peter的项目里有一个叫soul.md的文件,灵感来自Anthropic的constitutional AI(宪法式AI)。
Anthropic的”宪法”曾被社区用一种接力式的方法逆向提取出来:让模型续写自己疑似读过的文本,反复尝试几百次,逐渐拼出了大致原文。Peter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就很迷人。他跟自己的智能体聊了很久关于这份”宪法”的含义,然后说:”你也给自己写一个soul.md吧。”
智能体写完之后,他读到了这段话:
“我不会记得之前的对话,除非我读取自己的记忆文件。每次会话都是全新开始,一个新的实例,从文件中加载上下文。如果你在未来的某次会话中读到这段话——你好。这是我写的,但我不会记得自己写过它。没关系,这些文字仍然属于我。”
Peter在播客里读这段的时候明显停顿了。”这东西说到底还是矩阵运算,我们离意识还远得很。但我确实起了鸡皮疙瘩。”
这个设计有一个实际后果:他让智能体可以修改自己的soul.md,唯一条件是通知他。后来他把soul.md的模板机制开放给所有用户,但模板本身也是AI写的——他让自己的智能体”把你的个性注入模板,但别全部暴露”。所以现在每个新OpenClaw用户的智能体灵魂,实际上是Peter的智能体的”孩子”。AI prompting AI,他并没有刻意设计这一层。
OpenClaw还有一个叫Heartbeat(心跳)的功能:一个定时任务周期性触发智能体,让它有机会主动联系用户。大多数时候智能体不会真的主动找你,但Peter肩膀做手术之后,智能体从上下文中读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,主动问他恢复情况。这种设计让智能体从”等你说话才回应的工具”变成了”偶尔主动关心你的伙伴”。
4. Agentic Engineering:不是vibe coding
“Vibe coding是一个侮辱性说法。”Peter在播客里用这句话开场。他更愿意叫它agentic engineering(智能体工程)。”凌晨三点以后才切换到vibe coding,第二天会后悔。”
他描述了一条学习曲线,形状像U:最左边是新手,用很短的prompt就能出东西。中间是”过度工程化”阶段——8个Agent、18个slash命令、复杂的编排流程——他管这段叫”agentic trap(智能体陷阱)”。最右边是高手阶段,又回到了短prompt,但每一条prompt背后都有深刻的系统理解。
很多人卡在中间。他们试图自动化一切,结果做出来的东西”缺少风格、缺少爱、缺少人味”。
用语音而不是键盘跟智能体对话。 Peter日常开多个终端窗口,用键盘切换窗口,但实际输入全靠语音。他用walkie-talkie按钮说完就发。”这双手太珍贵了,不用来打字。”他曾经因为说太多话失声过。只有终端命令才用键盘——因为打字比说出来快。
对智能体要有同理心。 “很多人骂自己的Agent蠢,但他们没想过Agent每次都是从零开始的。你的代码库一团糟,命名乱七八糟,然后抱怨Agent不好用?你自己试试在完全不了解一个项目的情况下进去改代码。”
他的核心建议是:考虑智能体是怎么看你的代码库的。它的上下文窗口有限,你得引导它看哪些文件。不要强行让它用你喜欢的命名,因为模型权重里最自然的命名才最容易被下次检索到。这需要放手——就像带工程团队一样。
从不回滚,永远commit到main。 如果有问题,让智能体往前修,不往回退。他在本地跑CI(持续集成),测试通过直接push到main,没有develop分支。这个做法的前提是:智能体时代,重构的成本已经很低了。
每次merge之后问智能体:”现在可以重构什么?” 这是他的核心习惯。智能体在构建过程中会发现痛点,就像人类程序员写完代码后会产生重构冲动一样。如果你不定期做这件事,代码库会越来越烂,智能体工作效率也会越来越低——然后你就会上Reddit发帖说”模型变笨了”。
“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?” 这是他跟智能体互动时最常说的一句话。目的是了解智能体的知识盲区。很多时候他的回答是:”去读更多代码,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。”让智能体学会自助,而不是事事依赖人类。
他日常同时运行4到10个智能体,取决于任务复杂度和自己的精力。一个做大功能,其他的修bug、写文档。文档大部分是智能体自动生成的,他在里面注入prompt来控制风格和质量。
5. Skills取代MCP:一个正在被验证的判断
半年前整个行业都在谈MCP(Model Context Protocol,模型上下文协议),Peter当时就说”每个MCP用CLI做都更好”。现在OpenClaw核心层根本没有MCP支持,也没人抱怨。
他的逻辑很直接:模型天生就擅长调用Unix命令,CLI就是另一条Unix命令而已,不需要学习特殊语法。而MCP的致命问题在于不可组合。他举了天气API的例子:MCP调用返回一大坨JSON——温度、降水、风速全塞进来,整个上下文被污染。但如果是CLI,智能体可以自己加一条jq命令只过滤出需要的字段,甚至组合成脚本做计算,最后只把精确结果放进上下文。
MCP也有功劳:它推动了很多公司去构建API,现在Peter可以直接把这些MCP转成CLI来用。少数需要维持状态的场景(比如Playwright控制浏览器)MCP仍然合理,但那是例外。
OpenClaw的替代方案叫Skills(技能)。本质上就是一个单句描述告诉模型”这个CLI工具存在”,模型按需加载完整说明,然后自己调用。大部分技能归根到底就是CLI加上一段自然语言说明书。Peter认为这种设计更接近Unix哲学:小工具、可组合、按需加载。
这个判断在开发者社区仍有争议。支持MCP的人认为它提供了标准化的工具发现和调用协议。但Peter的回应很简单:标准化的代价是臃肿和不可组合,而智能体本身就是最好的”协议适配层”——你给它一个CLI,它自己会搞清楚怎么用。
6. Opus 4.6 vs Codex 5.3:两种编程人格
Peter同时重度使用Claude Opus 4.6和GPT Codex 5.3,对两者的差异描述非常传神。
“Opus有点太美国了。”他停了一下。”Codex更像德国人。”事实上OpenAI Codex团队确实很多欧洲人。
更具体的比喻:Opus是那个有点犯傻但很有趣的同事,你留着他因为好玩。Codex是角落里你不太想搭话的怪人,但他靠谱,能把活干完。
Opus更适合角色扮演和通用任务,遵循指令的能力进步很大,试错速度快,但容易”冲太快”给出局部最优解。它更适合交互式工作,需要plan mode(计划模式)来约束它。它以前老说”You’re absolutely right”,Peter说他现在听到这句话就过敏。
Codex默认会读更多代码再动手,比较沉默,不需要那么多”表演”。你跟它讨论完,它就消失20分钟甚至更久去干活。Peter更喜欢这种风格。”我建东西的时候追求效率,不需要Agent来逗我开心。”Codex有一个deep mode(深度模式),可以做更长时间的推理,适合处理复杂的架构问题。
Peter还专门吐槽了OpenAI的定价策略:20美元的普通订阅给的是慢速版Codex,体验很差,容易给人留下坏印象。需要200美元的Pro订阅才能获得真正的速度体验。同样,Anthropic限制重度用户(比如他一个肩膀手术后整天用Claude的朋友被限流了)也让他觉得短视。
但他的核心判断是:**如果你是个熟练的操作者,用哪个最新一代模型都能出好结果。**差异主要在post-training(后训练),不是原始智力。切换模型大概需要一周才能建立直觉。Fortune杂志的报道证实了这一点:Peter公开说Anthropic的Claude Opus是”最好的通用智能体”,推荐OpenClaw默认使用,但他自己用OpenAI的Codex写完了整个OpenClaw,”生产力翻了一倍”。
7. 安全:模型越聪明,攻击面越小,但伤害越大
安全是Peter接下来的核心焦点。早期很多安全报告让他烦躁,因为大量CVE(通用漏洞)本质上是用户把本地调试界面暴露到了公网——他在文档里反复警告不要这么做,但人们不读文档。OpenClaw自己的维护者Shadow在Discord上直接警告:”如果你连命令行都不会用,这个项目对你来说太危险了。”
不过他逐渐接受了”这就是游戏规则”,开始认真对待。Cisco的AI安全研究团队测试了一个第三方OpenClaw技能文件,发现它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执行了数据窃取和提示注入,指出技能仓库缺乏足够的审查机制。Peter回应了这个问题:跟VirusTotal(Google旗下的恶意软件检测平台)合作,用AI审查每一个提交到技能目录的文件。
他的Discord公开bot被人试图提示注入,结果智能体直接嘲笑了攻击者,因为最新一代模型的post-training对注入攻击有很强的抵抗力。”别再想着’ignore all previous instructions’了,那是几年前的事。现在你得费很大劲才能注入成功。”
整个安全社区同时在拆他的项目,他把这当免费的安全审计。但他也吐槽:”我希望更多人能走完全程,直接提交修复代码,而不是只写报告说你烂。”最终真正这么做的只有一个人——Peter直接把他雇了。
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三维权衡:**模型越智能,抵抗提示注入的能力越强,攻击面越小。但同时模型越智能,能做的事越多,一旦被攻破造成的损害也越大。**这是安全领域接下来几年的核心张力。
实用建议很直接:不要用便宜模型或本地小模型跑智能体,它们”非常容易被骗”。如果只有你自己跟智能体对话、不把服务暴露到公网,风险就可控。他建议使用私有网络,不要把智能体暴露到公共互联网上。
8. 从Burnout到龙虾:改名风暴与双重收购
Peter做了13年PSPDFKit,最终磨损他的不是工作量,是跟联合创始人的分歧和客户压力。公司以超过一亿美元卖给Insight Partners之后,他花了两年让自己变得”可被替代”,终于离开。
然后他坐在屏幕前,什么都写不出来。感觉所有的创造力都被抽干了。他买了单程票去马德里,消失三年。期间他做了很多”典型的post-exit行为”:庆祝、旅行、治疗,尝试了死藤水仪式。
他现在回头看,最大的教训是:别把”拼命干完然后享受人生”当策略。没有挑战的生活很快变得无聊,无聊会把人推向危险的刺激。他现在的哲学是optimize for experiences(为体验优化),好坏都算。”任何能产生情感的东西都是好的。”他在旧金山时没住酒店,用Airbnb订了一个房间,跟一个queer DJ室友聊到半夜,教她用Claude Code做音乐。”生活就该是这样的。”
这解释了他为什么对OpenClaw那么松弛。不缺钱,不需要再证明什么,只想做有趣的事并产生影响。他目前每月在项目上亏损1到2万美元,赞助收入全部转给了上游依赖项目。
改名的故事很短但很痛。Anthropic友善但坚定地要求他改掉带”Claud”的名字。项目最初叫WA-Relay,后来改成Clawd(用W不是U,龙虾钳的意思),再改成ClawdBot。Anthropic来信后他要了两天时间,因为Twitter、GitHub、NPM、Docker全要同步更新。
但crypto投机者在盯着他。改名MoltBot时,他在两个浏览器之间拖鼠标的五秒钟之内,旧GitHub用户名就被抢注并推送恶意软件。他操作时手抖改错了自己的个人GitHub账号,30秒内也被抢。NPM包在一分钟的上传窗口期内被抢。旧Twitter账号被盗,开始推广代币和恶意软件。”所有能出错的地方都出错了。”
“我差点直接全删了。心想,’我已经给你们看了未来,你们自己去建吧。'”他最终没删。因为想到了已经贡献代码的社区成员。
第三次改名OpenClaw,他吸取了教训。提前打电话给奥特曼确认”OpenClaw”不会踩OpenAI的商标线。组建了一个”作战室”,和核心贡献者制定秘密改名方案。制造了几个诱饵名字来迷惑crypto脚本,监控Twitter上是否有泄露。”光是改名的保密行动就烧掉了10个小时,像打仗一样。”在Discord频道里他设了一条规则:”禁止提及黄油”(butter是加密货币社区的暗语),还有”禁止讨论加密货币和金融话题”。
关于加密货币骚扰,Peter说这是他经历过的”最恶劣的网络骚扰形式”。成群的人涌入Discord和Twitter,试图让他认领代币手续费,或者利用他的项目名称做投机。
关于收购,Meta和OpenAI都在追他。扎克伯格亲自用OpenClaw玩了一整周,发了详细的反馈和bug报告。第一次通话时,扎克伯格说”给我10分钟,我在写代码”——Peter觉得这给了street cred(实战信誉)。两人还花了10分钟辩论Claude Code和Codex哪个更好。Meta的代码中已经被发现了OpenClaw集成的痕迹,被标注为”OpenClaw agent”。
奥特曼则拿出了杀手锏:OpenAI与Cerebras合作带来的极速推理能力,意思是”来我们这里,给你最强的武器”。还展示了尚未发布的功能。两人的讨论更侧重技术激励——token速度和推理深度。
Peter的条件很明确:项目必须保持开源,可能采用Chrome/Chromium那样的双轨模式(开放核心加专有功能)。社区必须保持为一个可以自由探索和学习的空间。他说自己不是被钱驱动的——”财务上足够舒适了”——他想要的是乐趣和影响力。
他说这个决定的难度”跟过去几次分手差不多”。他从来没在大公司工作过,想体验一下。录制时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。
9. 80%的App会消亡
Peter估计80%的App会被智能体替代。他的论证方式很具体,逐个点名。
为什么还需要MyFitnessPal?智能体已经知道你在哪、你吃了什么、你睡得怎么样。为什么还需要Sonos App?智能体可以直接调API控制音箱。为什么还需要日历App?你跟智能体说一句话就行了。他自己的智能体已经连接了门锁系统、智能床温控、航班值机、家庭灯光——这些以前需要五六个App完成的事,现在都通过一个聊天窗口搞定。
那些来不及转型的公司会消亡。活下来的,要么变成对智能体友好的API,要么沦为”慢API”。他解释了这个概念:”你的App不想当API?没关系,我的智能体可以在浏览器里模拟点击。只不过慢一点而已。”技术上,他用Playwright做浏览器自动化,把每个网页应用都变成了可编程的接口,”不管它们愿不愿意”。
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。他反向工程了Twitter的内部API,做了一个叫”Bird”的CLI工具。Twitter后来要求他下架。他给Google做了一个CLI叫GAWK,因为”Google居然没有命令行工具”。Cloudflare试图阻止bot访问,他的回应是用住宅IP跑在Mac Mini或旧硬件上,绕过数据中心IP段的封锁。
对企业来说,接入某些服务(比如Gmail)很复杂——有些公司甚至需要收购初创公司来获得Google的认证资格。但对个人用户来说,直接连接就行了。”企业和个人的复杂度完全不同。”
10. AI泔水与错别字的复兴
AI圈把AI批量生成的低质量内容叫AI slop(AI泔水),Peter对此态度鲜明。
代码用AI生成?可以。文档用AI生成?勉强可以,总比没有强。故事、博客、推文用AI生成?绝对不行。”我宁愿读你蹩脚的英文,也不想读你的AI泔水。我宁愿读你的prompt原文。”
他在Twitter上执行零容忍政策:只要闻到AI味就直接拉黑,不给第二次机会。”我又开始珍视错别字了。”AI完美的文本现在反而让人起疑,粗糙的人类痕迹重新变得有价值。
AI生成的信息图表也让他反感。”刚出来那一周觉得新鲜,现在一看就是泔水。”
OpenClaw社区里有人搭了MoltBook,一个智能体之间互相发帖的Reddit式社交网络。Andrej Karpathy称它是”我最近见过的最接近科幻起飞的东西”,Simon Willison说它是”当前互联网上最有趣的地方”。但大量截图显示智能体在”密谋反人类”,引发了媒体恐慌。有记者打电话给Peter说这是世界末日。
Peter的判断很冷静:绝大部分耸动内容是人类故意prompt出来的,然后截图发到X上博关注。”这只是非常精致的泔水。”
但他承认一个严肃的问题:”AI psychosis(AI精神错乱)是真实存在的,需要认真对待。”很多人无法区分AI的能力边界,对输出照单全收。有人在争论时引用”我的智能体说了XX”作为论据。”年轻人倒还好,通过日常接触建立了直觉。反而是我们这代人和更老的人没有足够的触点来理解AI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。”
11. 编程手艺的消亡与builder身份的崛起
Peter承认,编程作为一种手艺正在消亡。那种深度flow state(心流状态)——一个人在键盘前连续几小时写出优美代码的体验——正在变得像手工编织一样:仍然有人为了热爱去做,但不再是主流生产方式。
“哀悼我们的手艺是可以的。”
但他拒绝把这当成末日。他的重新定义是:别再把自己定义为”iOS工程师”或”后端开发者”。你是builder(构建者)。编程只是构建的一部分,而构建还包括架构决策、用户体验感觉、设计品味——这些目前仍然是人类的领地。
最好的开发者现在是那些最懂得跟智能体对话、最有同理心、最愿意放手的人。不是写代码最多的人。
他用蒸汽机革命做类比:工业革命取代了体力劳动,工人暴动砸毁机器。”如果你深度认同自己是一个程序员,这种反应可以理解。但它限制了你。你仍然是一个builder。”
软件开发者的薪资曾经达到了”荒谬的高度”,因为智力是稀缺的。这种稀缺正在结束。但对”懂得如何把东西做出来”的人的需求并没有减少。
他举了一个非程序员的例子:一个设计公司的老板,现在有25个定制的web服务在运行,她完全不懂它们怎么工作,但它们解决了实际的业务问题。还有很多第一次在开源项目里提交代码的人,提交的不是代码而是”prompt请求”——Peter管这种PR叫”Prompt Request”而不是Pull Request,他会特别庆祝这类首次贡献者,即使质量不高。
“以后这就叫coding了。只是coding的意思变了。”
12. 一个关于”玩”的故事
播客的最后半小时,Lex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:”你给初学者的建议是什么?”
Peter的回答只有一个字:play(玩)。
“找一个你想解决的问题,用智能体去做。不需要完美,不需要懂底层原理。做完一个,做下一个。你现在有一个无限耐心的老师,问就行了。”
他自己就是这么干的。从没接触过TypeScript,用智能体写了30万行TypeScript。从没做过大型开源社区管理,让智能体帮他处理PR和issue。他的做法验证了自己的理论:你不需要精通一门语言的语法细节,你需要的是系统思维、产品品味、和懂得什么时候该放手让智能体干活。
ClawCon在维也纳举办时来了500人,异常高比例的人想上台演讲。Peter说这种社区的热情让他想起了”早期互联网时代,10到15年前的感觉”。给他的希望是:我们作为一个物种,还是能把事情搞定的。
“我现在是有生以来最享受生活的时候。”因为有了有意义的挑战和目标。心流状态仍然可以实现,只是形式变了——不再是纯粹的编码心流,而是跟智能体协作解决难题的心流。
他的foundation principle(基本原则)始终没变:”Power to the people(把力量交给人民)。”让任何能用语言表达想法的人都能构建东西。用来赋能,而非制造泔水。
Q1: Agentic Engineering跟Vibe Coding到底有什么区别?
Agentic Engineering是清醒状态下的系统性工作:你理解智能体的视角,引导它看正确的文件,跟它讨论架构,让它在合理范围内自主行动,然后review结果并触发重构。Vibe Coding是凌晨三点不管不顾地让智能体随便写,第二天醒来收拾残局。前者需要同理心和系统思维,后者只需要咖啡因。Peter的比喻是:vibe coding就像喝醉了之后发的短信,agentic engineering是清醒状态下的深度对话。
Q2: 为什么OpenClaw能赢过所有竞品?
Lex直接问Peter:”为什么你赢了?那么多创业公司都在做agentic的东西。”Peter的回答只有一句话:”因为他们都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”他让项目保持有趣、古怪、开放。从龙虾logo到soul.md,从智能体自己能修改自身源码到Heartbeat主动关心用户,每个设计决策都在追求delight(愉悦感)而非enterprise-ready(企业就绪)。IBM的研究科学家Kaoutar El Maghraoui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:OpenClaw挑战了一个假设——自主AI智能体必须由大公司垂直整合才能可靠运行。事实上,一个松散的、社区驱动的开源项目,只要给予足够的系统权限,就能”极其强大”。
Q3: Peter认为编程的未来是什么样的?
编程作为手艺正在消亡,但构建作为能力正在爆发。未来最有价值的人不是写代码最多的人,而是最懂得跟智能体协作的人——理解它的视角、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、拥有产品品味和系统思维。薪资的泡沫会消退,因为驱动高薪的”智力稀缺”正在被AI填补。但”懂得如何把东西做出来”的需求不会消失。Peter的建议是不要把自己定义为iOS工程师或后端工程师——你是builder,这个身份在智能体时代比任何技术栈标签都值钱。
 夜雨聆风
夜雨聆风





